老人們,忙農(nóng)活做家務(wù)、帶孩子打紙牌,不少六七十歲的“年輕”老人,還在打零工補(bǔ)貼家用。在為老齡化社會憂愁時,老人們依舊努力保持活力,為社會、為家庭發(fā)揮余熱。
六七十歲的農(nóng)村人“不算老”
當(dāng)收割機(jī)放倒一片片水稻時,村里的老人們便惦記著要去哪家收稻草了。在如東縣馬塘鎮(zhèn),稻草可以搓成草繩賣,村民們可舍不得燒。家里有老人的,稻草曬干后留著自家用;沒老人的,就會放在地里,等著被人運走。
“一畝地稻草搓成草繩能賺400元左右。”徐莊村72歲的葛家夫正在地里忙著捆草,每捆約20斤重。一眼望去,田野里滿是1米多高的草捆,仿佛站崗的士兵。稻草曬干捆好,葛家夫就用板車往家運,在后院堆好,閑時和老伴一起用搓繩機(jī)將其搓成繩。
“一年能搓20畝地的稻草,賺萬把塊錢。”葛家夫說,如果一天搓8小時,他和老伴差不多能搓4捆,每捆收益18元。當(dāng)然,他們不是村里搓的***多的,有人家靠搓草繩一年能賺一萬五甚至兩萬元。“我們不靠搓草繩生存,干得動就干,干不動就歇。”
葛家夫的兒子葛飛在外跑運輸,這些天也在家?guī)椭细赣H農(nóng)忙。“老婆在企業(yè)打工,兒子在浙江當(dāng)兵,我不差父親這點錢。”壯實的葛飛招呼記者坐下,遞過一瓶紅茶飲料。黑黝黝的皮膚,如其老父。
見有記者過來采訪,葛飛家涌進(jìn)幾個看熱鬧的鄰居,清一色的老人,其中一位老婦,頭發(fā)白得如深秋的蘆葦花,不說話,只是瞇著眼睛聽別人講。“做個‘打草人’,也算給自己找點事做,發(fā)揮余熱吧。”葛家夫笑著說。
談及養(yǎng)老時,父子倆對視了一眼,又看了一下那位老婦,有點猶豫。“我這一輩,老人肯定我養(yǎng)。等我老了,估計就得去養(yǎng)老機(jī)構(gòu)了。”吸了口煙,葛飛嘆了口氣說,“在農(nóng)村,真正照顧老人的時間不會太長。因為只要他們還能動,就會一直忙,多少幫子女做點事。”話音未落,那位老婦已轉(zhuǎn)身離去。
“她家兩個兒子,沒一個養(yǎng)他們,老***倆還是自己過,都快80歲了。養(yǎng)老的話題,對她來說太敏感。”葛飛告訴記者,在農(nóng)村,要是有兩個以上孩子,養(yǎng)老大多是扯皮的事,很多老人真的是“老無所依”。“對他們來說,搓草繩是難得的經(jīng)濟(jì)來源,老兩口沒日沒夜干,一年能掙2萬元。”
與葛家夫握手道別時,記者的手掌被扎了一下。那是一雙布滿老繭的手,裂開了一道道口子。離葛家夫家100米處,有間孤零零的低矮瓦房,正是那位老婦的住所,她正呆呆地看著地里的稻草。見記者來,她假裝有事,下地忙活去了。那滿面滄桑憂郁,那蘆葦花似的頭發(fā),看得人心疼。記者不忍打擾,扭頭離去。
在種田之余,老人還能靠編草繩獲得額外收入,這得益于當(dāng)?shù)貛准也葜破泛献魃纾撬麄儼l(fā)現(xiàn)了商機(jī),并組織村民生產(chǎn)。65歲的葛家明,是如東利民草制品**合作社社長。他的合作社覆蓋馬塘及周邊幾個鄉(xiāng)鎮(zhèn),社員超過1000人,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。“我們合作社每年能消耗3萬多噸稻草,相當(dāng)于把4萬畝田的稻草變廢為寶了。”葛家明說。
追求自身的社會價值
每個人,都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(rèn),老人也不例外。農(nóng)村的老人,除了田間耕作帶孩子,也想法子多掙些錢;城里的老人,除了帶孩子拉家常,很多人投身于社會公益事業(yè)。
2001年,在如東縣關(guān)工委的支持下,退休教師繆云山聯(lián)合其他幾位退休教師成立了芳岑志愿服務(wù)站,假期是他們***忙碌的時候。繆云山告訴記者,10多年來,就是這些平均年齡近80歲的老人,為6000多人次的孩子舉辦了冬令營和夏令營,而這些孩子,一半以上都是留守兒童。
隨著外出打工增多,越來越多的學(xué)生不得不跟祖輩生活,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心理健康成長。這些校外輔導(dǎo)團(tuán)體組織的系列活動,為孩子們彌補(bǔ)了部分缺失的愛。如今,如東開展校外輔導(dǎo)的社會力量有***十支,近4000名留守孩子受到校外輔導(dǎo)教育。“感到***有成就的事,就是陪著這群孩子了。”繆云山說。
“他們并不在乎得到多少經(jīng)濟(jì)回報,而是追求自身的社會價值。”如東民政局副局長崔紅霞說,很多退休醫(yī)生和退休教師,整天都忙得不亦樂乎,真正實現(xiàn)了老有所樂。
72歲的洪劍高,是岔河鎮(zhèn)迎春社區(qū)支部書記,從1969年至今,由蔬菜大隊隊長到迎春村村長,再到迎春社區(qū)支部書記,村民們離不開他,他也離不開工作崗位。洪劍高很倔,1984年分田到戶時,政策要求將所有集體資產(chǎn)分光,但他堅持只分與生產(chǎn)有關(guān)的物資,而把隊里的房子用來出租。“集體有收入,才可能用來為農(nóng)民服務(wù)。”洪劍高說,有了集體收入,現(xiàn)在才可能為不斷老去的菜農(nóng)發(fā)點生活補(bǔ)貼。
如今,社區(qū)500多位菜農(nóng),三分之一是60歲以上老人。靠集體收入,菜農(nóng)每月的補(bǔ)貼,從3元、5元增加到現(xiàn)在的10元,盡管不多,卻是洪劍高手里的“一把米”,社區(qū)的老人們,似乎也多了點依靠。更何況,洪劍高還用這“一把米”為村里修路、鋪設(shè)自來水管線,每年組織菜農(nóng)們外出觀光旅游,甚至報銷部分醫(yī)藥費。洪劍高儼然成了“老黃忠”,盡管年事已高,依然不停地為鄉(xiāng)親們操勞。
掘港鎮(zhèn)三元社區(qū)的“愛心存折”也很有意思。所謂“愛心存折”,就是將志愿者的服務(wù)時間、服務(wù)內(nèi)容等信息記錄在“存折”上,等將來志愿者本人或其直系親屬需要義務(wù)服務(wù)時,再將記錄過的服務(wù)加以返還。三元社區(qū)黨總支書記王莉莉說,志愿者中有相當(dāng)一部分是“年輕”的老人。他們?yōu)椤澳昀稀钡睦先颂峁┓?wù),實際上是儲蓄了服務(wù),當(dāng)他們“變老”需要幫助時,再從“存折”里提取。
“老人樂土”離不開親情呵護(hù)
人間自有真情在。當(dāng)看到那些健康的老人、“年輕的”老人依舊在實現(xiàn)各自的社會價值時,記者的內(nèi)心暖暖的。可是,當(dāng)接觸到李明(化名)夫婦時,那種暖意很快蕩然無存。
93歲的李明是退休職工,每月退休金2400元,92歲的老伴是退休教師,每月退休金4300多元。11月初,他們從一家老年公寓搬到另一家老年公寓,每人繳了1635元,準(zhǔn)備住一個月再等兒子拿主意。“那邊沒人氣,也沒人來看我。”李明說,年齡大了,經(jīng)常會有個頭疼腦熱的,但在前一家老年公寓,量個血壓也要走三里路,所以住了不到一個月,就打電話給兒子的同學(xué)張翔(化名)幫忙搬了過來,“這里好,看病方便。”
只因曾是老人小兒子的同學(xué),張翔便成了李明在如東的依靠。他為老人的遭遇抱不平,也為老人的一些糊涂做法惋惜。
原來,李明夫婦育有兩兒一女,大兒子已去世,女兒也退休了,小兒子在外地工作,老兩口多年來一直由大孫子照顧。去年春節(jié)前,小兒子回如東,老兩口鬼使神差地將30萬元存折給了小兒子。“可他們的兒子連年夜飯都沒吃,就跑上海過年去了,留下老兩口在家苦巴巴盼著。”張翔認(rèn)為,老人的做法很糊涂,因為小兒子家很富裕,根本不缺錢。大孫子原來也沒惦記老人的存款,但老人將存折交給小兒子,大孫子認(rèn)為他們不把自己當(dāng)親人,拒絕繼續(xù)照顧。
后來,張翔幫老人找了保姆。保姆是當(dāng)?shù)剞r(nóng)村人,家里也有很多事,經(jīng)常連老人的一日三餐都無法保證,兩位老人只能以餅干度日。10月份,張翔把兩位老人安排到了老年公寓,11月轉(zhuǎn)到另一家。“聽說能換地方,老人早上三四點就把東西收拾好了,眼巴巴地等我去接。”
小兒子對父母的遭遇根本不聞不問。搬公寓后,張翔把新住所拍成照片發(fā)給他,只收到“你說好就好”的回復(fù)。對小兒子的做法,李明自言自語:“他工作忙得不得了,也很愧對我們。兒媳婦剛升處長,工作也忙。我們原諒他們。”記者問老人下一步的打算,李明說要等小兒子回來拿主意,甚至奢望能把他們接到外地去。
“他不可能回來的,更不可能把你們接去。”張翔在一旁急得大叫。雖然耳背,李明肯定能聽得到,但他仍低聲嘮叨:“等兒子回來再說,等兒子回來再說……”
老人的小兒子,也快是老人了,他的未來指望誰?
“目前比較可行的,還是探索社會化居家養(yǎng)老,才能盡量讓老人晚年過得安逸些、平靜些。”崔紅霞認(rèn)為,居家養(yǎng)老需要一定的經(jīng)濟(jì)基礎(chǔ),同時老人也要舍得花錢購買服務(wù),“但目前在如東,花得起錢又舍得花錢的老人,比例還很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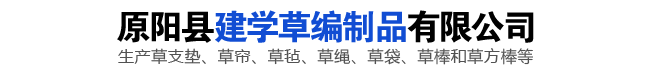



 豫公網(wǎng)安備 41072502000135號
豫公網(wǎng)安備 41072502000135號